1翻滾 羨慕嫉妒恨啊
朱慶義:話說我家親戚也有拆遷致富的,在拆遷之前,他們幾乎是靠我們的接濟過日。突然間,他們每一家都有了400多萬,卻開始看不起我們了!說我們老土,摳門,玩個牌上百的都不敢……
石頭一點點:我們這里開保時捷的清一色拆遷戶,不知道分了多少套房,反正人家干啥事都是:沒事,賣套回遷房就有了,牛氣得很,當個保安開X5上下班,哎……
龍翼:我認識一個農村人,拆遷后換了3套房子(姑娘一套,兒子一套,一套自用),一臺十多萬的車——我們城里人有啥?不說了,都是淚。求一畝三分地。

導語:在備受關注的“官二代”、“富二代”之外,這些年來“拆二代”群體越來越多地走進了輿論的視線。這個群體多數是出生在城市近郊的年輕人,他們在繼承了父輩們留下的房產,且實際擁有部分農村地產的情況下,恰逢城市發展機遇,由拆遷補償而實現了一夜暴富。
一片舊樓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來。每天,我們都會上演一幕幕關于拆遷引發的悲喜劇。“拆二代”這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可謂是成也拆遷,敗也拆遷。拆遷對于他們來說是天使,亦是魔鬼。來自于這個群體中的問題越來越多,已漸成為一種令人擔憂的社會現象。近幾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瞬間變成富豪,許多人曾經的家園,先是變成空地,接著又變成了CBD,這樣突來的富貴讓他們難以把持。這拆的不僅是房子,還有人心。
這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這些原本過著普通生活的人們,如今腰纏萬貫,身家數百萬上千萬者亦不在少數。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紛繁復雜的拆遷矛盾背后,那些急劇增加的財富,在提升他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給他們的家庭與人生帶來種種意想不到的危機。這就是我們目前大多數拆遷暴富人群的真實生活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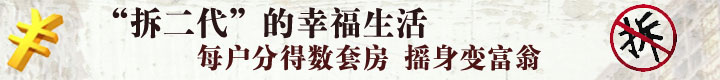
“拆二代”是工業化、城市化的產物。在《物權法》被人重視且農民權利意識越來越高的今天,僅從物質利益來看,遭遇拆遷也許已不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鄉愁之類是否留得住,哪里管得了那么多呢,至少拆遷補償所帶來的家庭存款、新房面積以及準城市化生活仍是令人艷羨的。
前幾天情人節的時候,有媒體用流行的“街采”方式要求被采訪對象對前任說句話,一個受到熱捧的神回復竟是:“我家馬上拆遷了”。可見,“拆二代”的幸福生活正是由拆而來的,有錢了,不僅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似乎也意味著很多事情都好辦了。比如年輕人的對象有著落了,一些人進行產業投資更有底氣了,這簡直是幸福來得太突然了。
奮斗篇: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多數“拆二代”很崇尚個人奮斗。
在房子拆遷之前,他們的父輩一般都很勤儉,他們也經歷過苦日子。在他們看來,多少家產也經不住坐吃山空,“家有百萬不如有個破店”。
一些學歷較低的“拆二代”,會考慮找個對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哪怕每個月收入一兩千元,也算有個正經營生;而大多數人,會選擇創業開店,一般會選擇飯店、洗車行、網吧等。
張秀是鄭東新區十里鋪的居民,分了幾套房子后,她租出去了一套,自己還開了一個洗衣店。張秀說,很多村里人都自己開旅館,而她則一門心思打理洗衣店,“天天閑著搓麻將可不是正事兒”。
更多學歷高、已經走出去的“拆二代”,更傾向于自己打拼,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黨力力家住鄭州市侯寨鄉,拆遷后,他們一家會分到5套房子。
今年27歲的她,到夏天就會拿到中山大學的碩士學位證書。黨力力想回鄭州發展,過完年,她就每天奔走在鄭州市的各個人才交流中心,希望謀得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其實黨力力家里的條件一直很不錯,父母都有工作,但她說:“人活著,總要有個奔頭,為自己喜歡的事多拼拼總沒錯。”
和黨力力不同,家住鄭州燕莊的女孩王新在上海讀完碩士以后,在當地一所中學當英語老師,每周末去培訓學校兼職代課,寒暑假會跟著公益組織去山區支教。
王新說,她喜歡外面的世界,也很感謝家里給自己提供的經濟支持,這讓她在追逐夢想的路上沒有后顧之憂。
“我已經是第二次被拆遷了,拆遷后補償款的浪費我都經歷過。”曾祥覬是運輸公司的法人代表,他經歷過兩次拆遷,2001年第一次拆遷時,他也獲得了一筆補償款,但沒用多久,錢就沒了,只能去城里打工。2012年,“拆遷富”的命運再次眷顧了他,他得到了數十萬元補償金。
曾祥覬說,村里有20多戶人家是做運輸的,村民自己有車輛,靠近工地也靠近自己的家,但就是苦于沒有穩定的貨源。有時候,拉貨還經常被拖欠工錢,所以就想著整合資源,把拆遷款盤活,組成運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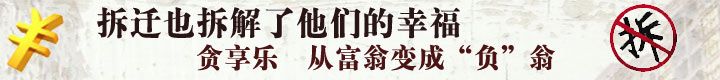
不過,“拆二代”在迎來突如其來的幸福之余,也會遇上一些新的問題:一些“拆二代”在暴富之后,心態也會隨之而變,可能會出現人生的迷惘期,比比皆是的炫富、奢侈消費、厭學、不思進取的現象,尤其容易讓他們迷失方向。“拆二代”所面臨的人生際遇不只是財富的突然增加,更是人生的突然轉型。這個轉型是被城市化大潮推著走的,是不期而來的,因為拆遷已經改變了過去的平靜的田園生活,過去窮則思變,窮則思進取的主流價值也可能在驟然到來的財富面前被迅速消解,新的價值觀又尚未定型,以至于許多人已無心思考下一步的人生走向何處。
許多“拆二代”甚至于還看不到坐吃山空的可能性。他們勇于爭取靜態利益,被眼前的財富所迷惑,卻怯于思慮創造未來,開創繼往開來的事業。顯然對眼前“拆遷財富”的揮霍,流失的不只是年輕且不能重來的日子,甚至于也是在一點點地“拆解”了自己的幸福。
迷茫篇:
吳蒙原先住在鄭州的都市村莊老鴉陳,拆遷之后,家里分了幾套房子,房租足夠養活家人。28歲的他每天在家炒炒股,上上淘寶,是一名標準的“宅男”。
朋友找他做生意,他覺得自己做不來;給他介紹過幾份工作,工地上的他覺得臟,公司里的他覺得不自由,慢慢地也沒人給他介紹工作了。
現在的吳蒙過得很愜意,但也很迷茫,“一直這樣下去也不是個辦法,但是我目前找不到啥突破口。”
和吳蒙一樣迷茫的,還有給一家公司老總開車的孫軍。
今年23歲的他,家住鄭州市航空港區薛店村,航空港區的建設占用了他家的地和房子,賠償費很可觀。家里給他買了車,他開著車去給公司老板當司機,而他的車比老板的還好,沒多久,老板把他辭退了。
如果僅僅是無所事事,也許還不會讓家人那么傷心。最讓人提起來就當成“負面典型”的,就是一部分揮霍家產的“拆二代”。
袁偉家住鄭州市區西邊的一個都市村莊。近幾年拆遷賠了不少房子,他父親做醫療器械生意,家里可稱得上是村里的首富。
“前兩年,他要買一輛價值100萬元左右的‘卡宴’,他父親不給他買。”袁偉的朋友張先生說,為這事兒,他跟父親鬧了很久。
父子吵架的結果就是,袁偉一氣之下喝了毒藥。搶救過來之后,袁偉的父親只好給他買了一輛“卡宴”。
“他就這么一個孩兒,能怎么辦呢?” 張先生說,袁偉一直沒有什么正式工作。“錢花完了,有家人給他拿呢。”
為了讓袁偉早點收心,家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在銀行工作的女友。“那女的長得很漂亮,家境也很好,倆人很快結了婚。”
去年,這個女孩兒跟袁偉離婚了,原因是袁偉經常不回家,天天在外面花天酒地。
他是黔西縣上馬村的失地農民張力(化名)。去年,他獲得了近百萬元的巨額補償款。那時候,村民們興奮樣、相互遞煙道喜的場景,他依然記憶猶新。而面對突然的“幸福”,一些村民又在肆意揮霍中迅速消失殆盡,如今張力背上了近10萬元的外債。
銀行卡里的錢無非是個數字而已,數字增減間,他們都覺得非常刺激。
紙醉金迷了一陣子,張力盤算著以錢生錢,打麻將、買六合彩……賭注一天比一天大,最多的一個晚上贏了十多萬,最慘的一個晚上也輸了十多萬。
很快錢輸光了,自己的生活也被套牢了,媳婦帶著孩子走了,張力、陳貴才向其他村民借高利貸,找親戚要錢,繼續賭繼續輸,結果兩人現在都欠了10多萬的債。
劉巖(化名)今年22歲,家住湘潭九華工業園拆遷安置小區。之前他在一家工廠打工,去年拆遷款發下來后,劉巖就把工作辭了,開著一輛紅色的馬自達回到了村里,坐在車里的還有一個18歲的女孩,他向鄰居介紹說是女朋友。可不到半年,他車里的女朋友換了5人。
村民介紹,村里像劉巖這樣的伢子還有不少,都是隔三岔五就換個女朋友,讓人看了瞠目結舌。
長沙市岳麓區洋湖垸的征地拆遷開發始于2008年,涉及拆遷對象大約有1309戶。失地農民均被安置在有“長沙市先導區首個保障性住房項目”之稱的洋湖景園,現年54歲的張德才(化名)就是洋湖景園的拆遷居住戶之一。
張德才一家6口人,洋湖垸被征地拆遷后,國家按政策給他一家安置了6套住房,平均每套房子有80平方米,全家人共得到170萬元的補償款,同時政府還為他們購買了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此后的張德才一家過得并不開心,這一切都源于他那個“不爭氣”的兒子。
據張德才介紹,自從家里得到170萬的征地補償款后,他的兒子小張就不再出去打工了,整天無所事事,跟一班朋友下餐館、進舞廳。剛開始張德才沒留意,覺得年輕人吃吃喝喝也算正常。但沒想到的是,小張竟染上了毒癮。“我就這么一個兒子,實在拿他沒辦法,這兩年被他揮霍的錢起碼有40多萬了,照這樣下去坐吃山空將來怎么生活啊。”張德才滿臉憂郁地說,居住在洋湖景園的吸毒青年,據他所知就有十幾人,“家里有錢了,年輕人不愿出去做事,結交了一班壞朋友就染上了毒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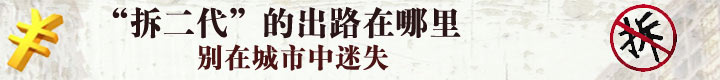
財富從天而至,許多人暫時還無心思考下一步的人生走向何處。許多“拆二代”還看不到坐吃山空的可能性。他們勇于爭取靜態利益,被眼前的財富所迷惑,卻怯于思慮創造未來。顯然對眼前“拆遷財富”的揮霍,流失的不只是年輕且不能重來的日子,甚至也是在一點點地“拆解”自己的幸福。
“拆二代”當下面對的最嚴峻的問題恰恰是如何實現向現代城市人的轉變。這是一個融入現代文明的過程。“拆二代”要想不被社會所邊緣化,不被時代所拋棄,尤其需要“立起來”。“拆二代”現在有了以前求之不得的財富,正好可以為立志轉型提供物質條件,顯然只有追求知識、智慧和創新精神,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讓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在“拆二代”們看來,這才是和城市接軌的真正出路。
鄭州市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陳寨,剛剛富起來時,因為村民整體教育水平低,村里就鼓勵上學,凡是考上大學的,每人補助兩萬元;凡是能出國留學的,每人補助5萬到7萬元,那幾年村里出了十多個留學生。
年輕的“拆二代”們,因為結婚較早,不少已經有了孩子。在他們看來,錢花到孩子的教育上,才是正經地方。
30歲的李昂,家里的房子位于鄭州市西郊,今年要拆了,屆時每人可分到一套150平方米的房子,外加30平方米的商鋪。
李昂初中畢業后當了幾年兵,回來之后,跟著親戚在工地干活。李昂說,這些房子的房租足夠家人生活,而他不想就這么下去。
李昂的孩子今年兩歲半了,提起孩子,他說:“我這一輩子也就這樣了,沒啥學問,但是我一定得讓我兒子好好讀書。”
要完善拆遷補償政策,不應一刀切地按面積、市價一次性補償巨款之后“甩手不管”。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得到相應的補償無可厚非,但是征到土地的政府不應只是簡簡單單地“授人以魚”。有關部門在實地調研后,可考慮分期付款;或者根據實際情況,規定一定比例的補償資金只有在特定用途,比如創業或者擴大原有產業規模的情況下才能提供;或者以村集體為單位建立有限公司,農民可選擇以補償款入股,政府給予稅收減免等優惠舉措,同時積極為其介紹聯系優質項目……這樣,政府可以引導農民補償資金的正確流向,使其資產保值增值。同時,公司的設立也為失地農民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

聽慣了強拆和“釘子戶”的對抗故事,以為拆遷總是伴隨著一些不和諧的因素,比如,推土機和燃燒瓶的對抗。然而,看到這篇《“拆二代”的幸福生活:每戶分得數套房,搖身變富翁》的報道之后,許多網友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原來,許多“拆二代”在失去了之前的家園后,實現了真正的破舊立新,搬進了更好的家園,不僅居住在以“苑”“綠洲”“都會”“豪庭”命名的現代化小區中,而且家產翻番,更因為補償款的到位而經營起了實業,成為傳說中的“資本家”。
“拆二代”的幸福生活,讓許多辛辛苦苦考上大學或考上研究生然后在大城市打拼多年,仍然在節衣縮食還房貸的同齡人們,產生了各種心理上的不平衡。更聯系到許多拆遷戶,開著豪車跑黑出租,經常性出入賭博場合等新聞報道,不少網友對“拆二代”們的幸福生活產生了一些羨慕嫉妒恨。在網上,更有這樣的道德綁架論者:他們不勞而獲,是社會的蛀蟲,也是懶蟲。
在筆者看來,“拆二代”們的幸福生活,是他們用正當而合法的生產資料換來的;在拆遷建設過程中,他們能夠獲得合適的補償款,在地方發展的過程中分得一杯羹,這是他們的福氣和運氣,也是他們的正當權利。這些權利,受拆遷條例和物權法的保護,是他們應該得到的。現代社會中,按土地等生產要素取得分配收入,既不違法,也不違背常理。他們出生在城鄉接合部或是離大城市較近的工業區附近,這是從他們一出生就決定了的,而附加在這上面的種種權利和福利,他們有權享有。
沒有做傷天害理的事,就不需要被道德綁架。而且,他們中的多數,也正在苦心經營著自己的資產。“拆二代”中的相當一批人是追求上進的。更加上,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他們以及他們的父輩在到底是做城市人與還是農村人之間產生過糾結,還要承受自己的家園率先變成工業區,面臨工業污染、拆遷補償不到位的各種擔憂。要知道,在強拆的新聞不時出現之下,即便新聞報道中有多少個拆遷成為億萬富翁、千萬富翁的案例,那些莫名的不安全感,仍然讓人恐懼。
對比而言,那些考入大學、留在大城市工作的白領,雖然過得比較拮據,但老家畢竟還有真正的宅基地—沒有成為潛力股,才是最大的潛力股。那些老家的宅基地,是不受70年限制的固定資產,而且,誰也說不準在什么時候面臨拆遷的機遇。即便是發展成為“家庭農場”(中央一號文件已經提出),在宅基地和承包地上,也是擁有一些權利的。如果他們的戶口所在地也在拆遷范圍內,他們也會成為“拆二代”,他們也擁有依靠拆遷實現致富的權利和機會。
現代社會中,與其對別人的發財致富之路羨慕嫉妒恨,不如過好自己的每一分鐘;與其關注別人拿到幾套房子和多少萬元補償款,不如看看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能否將這種資產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優勢。價值多元化的當下,比一時的生活壓力巨大或是生活幸福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擁有認真的生活態度以及是否擁有聊以自慰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
朱慶義:話說我家親戚也有拆遷致富的,在拆遷之前,他們幾乎是靠我們的接濟過日。突然間,他們每一家都有了400多萬,卻開始看不起我們了!說我們老土,摳門,玩個牌上百的都不敢……
石頭一點點:我們這里開保時捷的清一色拆遷戶,不知道分了多少套房,反正人家干啥事都是:沒事,賣套回遷房就有了,牛氣得很,當個保安開X5上下班,哎……
龍翼:我認識一個農村人,拆遷后換了3套房子(姑娘一套,兒子一套,一套自用),一臺十多萬的車——我們城里人有啥?不說了,都是淚。求一畝三分地。
憤怒的牛:我們村子拆村三年了,都沒有動工蓋回遷房,貌似村干部肥了。
平安祥和:有的拆成富二代,有的拆得家破人亡。
麗麗:北上廣深附近的拆遷戶更爽吧!
度度:與“官二代”、“富二代”相比,大部分“拆二代”在暴富前沒有一個逐漸擁有財富的過程,無論從心理上,還是從能力上來講,都沒有為擁有大筆財富做好準備。
丫丫:今年回去,家徹底變了,房子沒了,土地沒了,相親相愛的一家人也不齊了,為了點拆遷款,幾十年沒紅過臉的一家人,現在連面都不愿見了……拆遷是暫時給了我們一定的財富,可我們失去的是永遠找不回的東西,家人的勤勞質樸不復存在了!
馬駿-miles:我的房東七八年前還是個北京窮屌絲,一拆遷,12套房,立即不上班了,買了輛跑車,他兒子天天帶不同的漂亮女孩回家。每個月四萬多元的房租收入,培養的是垮掉的一代。人啊,儉以養德,沒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網易長春網友:在我們這里,領低保的有一半是昔日的拆遷戶。一般而言,拆遷后第一時間拆遷地就會出現賭場,就會有連夜輸掉所有拆遷款的人。然后陸續有人買車和高消費,一般三到四年就會有大批拆遷戶來社區訴苦,真正投資或投資成功的拆遷戶很少很少,能把拆遷款放銀行讓錢慢慢貶值的都算是有頭腦的了。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鳳凰網保持中立